骑士小说网 www.74xs.org,草莽英雄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。反倒用责备的口吻,大声说道:“你身为前敌主将,既然见得到此,何可坐视不救?”
俞大猷一愣,旋即恢复了平静的脸色“我尽我的力量。就不知道可不可能救得回来?”说罢,起身吩咐:“备马!”
“俞将军,”赵文华挽住他的衣袖问“你去督战?”
“不敢说。但盼田州土兵还没有跟倭奴接仗,能到青村与邹游击会合。等我到了那里,看情形再说。”
“如果已经接仗了呢?”
“那就凶多吉少了!如今只能盼望一个情况,田州兵的位置占得好,是在北面;那样子才有希望驱倭入海,然而,难,难!”
“怎么呢?你看田州兵不中用?”
“占地利,失天时。”俞大猷望一望空中“‘四月南风大麦黄’,田州兵如果占住北面,就是逆风作战,显然不利。”
等俞大猷赶到青村,局势已经为他不幸而言中了!通倭的那名向导,故意将田州土兵引入柘林之西,漕泾的一个渔村;倭寇海盗,早有埋伏,拦腰截击,将田州土兵冲作两段,前一段被包围;后一段为敌人的强弓硬弩所阻挡,进既不可,退又怕敌人临背追击,只能凭藉一片竹林,勉强守在原地,成了相持不下之势,而实有进退维谷之窘。
幸好俞大猷所派的传令校尉,跟后一段联络上了;于是折而往东北,退向青村一带。倭寇海盗的实力并不充足,持着“赊一千不如现八百”的想法,放过后一段,集中兵力去“吃”前一段。在青村,对于漕泾方面的战况,还不明了,但凶多吉少,已是不卜可知的了。
“邹兄,”俞大猷向刚从闽行来赴援的邹继芳征询意见“你看被围的田州兵,该不该救?救不救得回来?”
“救当然该救。不过救不回来,再拿救兵失陷在里头,就会牵动大局。将军,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。”
俞大猷暗暗点头。邹继芳的所见略同,便可以作断然处置了。“大局一定要顾到。壮士断腕,不失为明智之举。”他说“我们要防敌人乘机反扑,集中人马守几个口子。”
守几个口子,就是守大路上的几座桥。当时议定,两方面的兵力合在一起运用,邹继芳主外,带兵增强防务;俞大猷主内,安置吃了败仗的田州兵,不让他们的锐气折伤得太利害。
到了傍晚时分突围而出,成了散兵游勇的田州土兵,陆续由邹继芳派人护送到青村。俞大猷亲自带人照料,给食裹伤,殷殷慰问。同时问起战况,才知道900多人阵亡了一半,其中有14个头目,包括钟富在内,被俘与逃出来的,大约各为一半之一半。损失真是相当惨重了!
这是赵文华轻举妄动的结果。俞大猷责任所在,不能不星夜驰报张经。正在灯下与幕友商酌军报时,瓦婆婆由胡宗宪陪着,赶到青村看田州土兵和俞大猷。
两位来客的脸色不同,胡宗宪泰然,而瓦婆婆凝重,眼圈红红地,已经哭过一场。俞大猷本想责备她几句,这么大年纪,何以一点定力都没有,轻易听人指使?见此光景,改了口气,反倒要安慰她了。
“胜败兵家常事。”俞大猷亲自搀扶着她说“瓦婆婆不必难过!”
“我怎能不难过?我的娃子们死得冤枉!”瓦婆婆厉声说道:“倭寇海盗虽多,田州娃子拚得过他们,只可惜,紧要关头借不上力。”
俞大猷见她疾言厉色的神情,未待通事翻译,心知不妙;听完翻译,更知瓦婆婆是受了赵文华的先人之言,特来指责他不发援兵,这可得辩个清楚。
这是很可气的一件事,但俞大猷还是忍住了。一则,他到底读过些书,懂得养气的道理;再则,保靖兵已在途中,一旦到达,十道进兵,痛剿清洗,可以一劳永逸,当此紧要关头,真所谓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为了期望田州土兵还能大大地出一番力,此时当然需要安抚。
因此,他平静地答道:“瓦婆婆错怪我了!事先我并不知道贵部有进兵之议,今天一早由赵侍郎亲自来通知,立刻发兵支援,毫无耽搁。瓦婆婆请想,如果不是我派兵接应,贵部出击的队伍,何以都能齐集在此?”
听这一说,瓦婆婆无话可答。其实,她作此指责,亦是一种姿态,主要的是让她的部下知道,她是在替他们诉苦喊冤。坏是坏在向导身上,然而这又是个哑巴迷!向导秉命而行,钟富带队,究竟跟向导说了些什么?如今死无对证,再也分辨不清楚了。
“瓦婆婆,”胡宗宪当然知道自己误事,不过不能也不必承认,只安慰她说:“田州兵忠勇可佩!无论胜败,人死不能复生,只有打点精神,为阵亡弟兄报仇、雪耻。”
“打仗原是要死人的!”瓦婆婆答说“我难过的是,将帅心不起,我的娃子死得有点不明不白。这也不去说它了,如今我只有一句话:从今天气,田州兵不单独出队了!要打大家一起打。”
“原就是这话!”俞大猷赶紧接口“倘或瓦婆婆接到赵大人的命令,先跟我商量一下,就不会有这样的挫折了。”
胡宗宪在一旁默默听着,颇为后悔,应该劝赵文华慎重。如今听瓦婆婆的话风,有些变通了,不再是前两天那种报答恩遇,虽死不辞的态度。倘或追究此番失利的责任,只怕赵文华还真难辞其咎。
“怕什么,先下手为强!”赵文华的脸色很阴沉“让田州土兵出击并没有错,他们打得很好;坏在向导不得力。”他急忙又说:“这不能怪你,要怪他们;倘或不是按兵不动,自老其师,凡事可以商量,就可以找俞志辅去要向导,不就打了胜仗回来了吗?”
“是。”胡宗宪很沉着地问:“大人打算如何下手?”
“我要动张廷彝!”
“只怕动不了!”胡宗宪说“我看,保靖兵一到,也会打个大胜仗;那时候就该他神气了。”
“他要神气?神气些什么?”赵文华想了好一会,面露狞笑“你看我的手段!我要教他败了不得了;胜了更不得了!汝贞,你信不信?”
“大人的话,何有不信之理。不过,才具短,看不透大人的深处。”
赵文华已经想到一个说法,但正当要开口细谈时,忽然转了一个念头,自觉胡宗宪处处比自己强,即令他非常知趣驯顺,就眼前来说,决无遭受反噬之虞,却仍应拿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这两句俗语为戒。而且看他有些不明白,何以张经“打了败仗不得了,打了胜仗更不得了?”
那就让他纳闷去;等降罪张经的上谕下来,也教他看看自己的手段!
毕竟还是自己比胡宗宪高明!赵文华在心中得意自语,表面上却很矜持“也不知能扳得倒他不?”他说“尽力而为吧!”
等胡宗宪一走,赵文华随即将自己关在书斋内,静悄悄地草拟奏折,主旨是攻击张经拥兵自重,能够力战而故意不战;为的是可以不断向朝廷需索,向地方勒派,在粮饷上侵吞肥己,照张经的打算,寇如饥鹰,饱则远扬;到倭寇海盗撤退以后,张经才会追剿馀寇,假报大捷,虚冒战功。
这一来,张经如果打了败仗,倒可反证赵文华的奏劾,并无根据;一打胜仗,恰好证明了他的看法不错,坐实了张经有意冒功。
田州土兵的受挫,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恶劣影响。倭寇海盗对于在西南瑶壮苗子,了解不多,只当他们如同出押之虎,凶猛非凡,以趋避为吉。哪知一仗打下来不过尔尔!然则畏他何来?
就因为这一念的转移,便又大举骚扰掳掠;由海入江的南通州、狼山、常熟、江阴,无不大遭荼毒。警报一日数次,报到嘉兴,张经急得跳脚,除了大骂赵文华打草惊蛇,误国害民以外,别无作为。因为包围聚歼的方略是早经决定了的,一切部署都本着此宗旨进行,为山九仞不能功亏一篑,否则不就跟赵文华的浮躁轻率,有何不同?
而赵文华却放不过他。为了不愿看张经的“老前辈”的脸色,他只用文书督促;一天至少一通,甚至两通,三通,文书中的措词,大同小异,第一段是引叙战报,某处被侵,死伤多少,财产损挫几何?第二段是谈总督的责任是保境安民;捍御外侮;而张经受恩深重,决不忍坐视不问。第三段是恭维以后的指责,说某处某处乞援“督辕”不发一兵一卒;现在大军云集,不难灭此跳梁小丑。何以按兵不动,实难理解。
最后一段便是要求从速出兵,传述皇命以外,往往还要“为民请命。”
连损带嚣,文字犀利刻薄,张经看过一两通以后,气得再也不看了。当然也谈不到有何复文——这原在赵文华意料之中,明知不会有结果而乐此不起,无非为张经将来下狱受审时,留下许多不利的证据而已。
这样到了四月廿几,水顺、保靖的土兵终于开到了。永顺、保靖的土司都姓彭,一个叫彭翼南、一个叫彭盖臣,官号称做“宣慰使”都很能干,亦都善于带兵,部下久经训练,不容易打得散。不像田州土兵为乌合之众,能胜不能败,一败就溃。
这也就是张经必得等这两支到了,才肯动手的缘故。事先,张经将卢镗由浙东调到嘉兴,专门负责指挥永顺、保靖土兵;同时指定驻扎在无锡、常熟一带,因为大军云集浙西,地方负担过重;无锡、常熟等地亦是膏腴之地区,可以养得起这两支土兵。
在柘林至川沙的倭寇、海盗,本来有两万多人;一部分流窜各地,也还有15000人左右。他们也早就了解张经的方略,所以等永保兵一到,知道生死存亡所击的一场大战,迫在眉睫了。
就在这时候,汪直已由日本的五岛列岛,专程抵达柘林。此来本是观察动静,恰好赶上情势如箭在弦上之时,便顺理成章地作了发号施令的大头目。浙西的地形,他相当熟悉,在研判来自各地的谍报以后,发现官军的部署,着重在南面沿海自金山卫至海盐一线,以及北面的沿长江南岸各地,中路青浦、松江到嘉善、嘉兴各地,并没有多少兵力,而嘉兴是张经驻节之地,倘或能够发动奇袭,活捉张经,固然可以瓦解官军的整个攻势;即使不能如愿,至少张经会求调西龙两路的军队回嘉兴。那一来南面沿海的防务就会出现漏洞,岂非可乘之机?
这是先下手为强的做法,倭寇海盗的头目,全都赞成。于是汪直挑选了两千人,编成一支奇袭的队伍,在已过下弦,月黑风高的4月27,由青浦、松江之间的一条小路,往西直扑嘉兴。
在汪直到达柘林的第三天,胡宗宪即已知道这个“同乡”的行藏。以后,汪直定计以及从那一天气照计行事,亦无不了然。
是一个偶然的机缘,碰上一步鸿运,可也是胡宗宪内疚于心,力求补过的报酬——误用了那个汉奸作向导,以致于田州土兵吃了大亏,虽没有人公然指责,甚至还不知道他在无形中犯了极重的过失,可是胡宗宪却不能原谅自己。觉得唯有狠狠收拾倭寇海盗一番,才能使自己宁贴、他人尊重。
可是,他所能在军事上发生的作用不大。张经和李庭彝都已经对他怀疑,采取戒备的态度。想领一军好好打胜仗,已成妄想;张经甚至于连召集将佐,听取报告的集会,都不要他参加。这样,要想建功雪耻,就非另辟途径不可。
也是得来的灵感:敌人能派间谍到这面来,这面又何尝不可仿其道而行之,也派间谍到那面去?
难的是那里去找这样一个间谍?想来想去,只有同乡可以信任;因而微服私访,访的是一个典当的“档手”
“档手”就是掌柜的大朝奉。此人名叫胡元规,是苏松诸府中徽帮商人的领袖之一;也姓胡,与胡宗宪是五服之外的疏族,照家谱排辈分来,要矮两辈;胡宗宪行三,因此胡元规管这位比他小10岁的叔祖叫“三爹”
“三爹今天怎么得闲?”胡元规迎着他说“湘西的苗子开到了,快打仗了吧?”
“你知道湘西苗子来打哪个?”
听得这一问,胡元规心中一动,不过声色之间,毫无异样。“不是打倭寇吗?”他问。
“非也!打我们徽州人。”
“三爹,”胡元规急忙提高了声音说“今天我有真正的四鳃鲈,家乡又新来一个厨子。吃酒、吃酒!”
延至密室,胡元规方始明白相告,柘林与倭勾结的海盗,因为汪直的关系,颇多徽州人,经常潜入松江城内,到各当起来访同乡。他怕胡宗宪谈下去会涉及军事机密,泄露了非同小可,因而乱以他语。是一番谨慎的好意。
这就对路了。胡宗宪在想,开口便知不是汪直一党,尤其难得的是,谨密机警,正是可共腹心的人。因而便说了连在赵文华面前都不肯说的话,当然,也发泄了在他人面前不便发泄的牢骚。
“徽州人该死!到处挨骂。”胡宗宪愤然跺脚“开当铺,道是剥削小民,没有人说,救了穷人的急。如今为了一个汪直,我们徽州人在别人眼里,都是汉奸,不过——”他的声音突然软弱了,倒仿佛为人当胸捣了一拳似地“也难怪!”
“三爹!”胡元规扶着他坐在炕床上首,自己拉张骨牌凳坐在他身边,低声说道:“我也听了些闲言闲语,说张总督是福建人;福建沿海通倭的乡绅很多,张总督怕得罪他们,不敢上紧剿倭,如今莫非因为汪直是徽州人,大家也疑心三爹?”
“我不知道别人对我怎么个想法,只觉徽州人抬不起头来。”
“是的。”胡元规黯然摇头“没有法子!”
“怎么叫没有法子?什么是没有法子?”
“怎么能让徽州人抬起头来?我想想,没法子!”
“笑话!”胡宗宪的精神又振作了“如果徽州人不通倭,为什么抬不起头来?如果徽州人能够平倭,那就不但抬得起头,还可以扬眉吐气。”
胡元规倏然抬眼,怔怔地看着胡宗宪;四目相视,无形中出现了一种剑拔弩张的情况,而终于彼此都看到对方心里了。
“你有能让徽州人扬眉吐气的法子?”
“这还不敢说。不过,三爹,”胡元规说“也有同乡跟三爹的想法差不多;只不过没有三爹这样手握‘尚方宝剑’,想也是白想。”
“如今谅不是白想了!你们的想法,只要行得通,一切在我。”胡宗宪说“就怕不切实际!即使行通了,于大局无补,亦是枉然。”
其实,胡元规的一切,不免做作。有血性、重廉耻的徽州人,亦是不少,胡元规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有他们的为国除害、为乡雪耻的计划;但却不愿与官府合作,因为朝中奸臣当道,有作为的督抚,往往不为所容,结果徒受牵累——徽州人经营典当、经营盐业,都是有身价的巨商。一受牵累,事业瓦解,不仅仅“一家哭”;依附在这事业内外的人家,少则数十,多则数百,亦失所恃,这关系太重,不能不格外慎重。
然而胡宗宪的情况不同。第一、是徽州同乡,胳膊不会朝外弯;其次,他有才气、有气力,能办大事;第三、跟赵文华处得很好,一旦放手大干,朝中不会有人掣他的肘。可是,汪直也是同乡,胡宗宪对他的态度又如何呢?
如今是很明白的了,也很可以放心的了。不过,他亦不愿意将一场大功勋轻易送给胡宗宪,至少限度要取得胡宗宪的承诺,决不泄密,亦决不会独断独行,免得措施不善,累及同乡。
打定了主意,胡元规脸上自然而自然地出现神秘而郑重的表情“三爹,”他用低沉的声音说“我想告诉你一点事,不过要请三爹先在菩萨面前立誓,决不会害我们。”
胡宗宪听得这话,兴奋而困惑“你这叫什么话?”他说“我为什么要害你们?”
“不是说三爹存心要害我们,是怕无意中泄露一句话,或者举动稍疏忽一点,替我们招来冤家,那就家奇人亡有余了。”
有这样严重的后果,胡宗宪觉得他的要求并不过分。胡元规信佛,特辟一座院落,供设佛堂;胡宗宪拈香下跪,立下誓言,决不相负。然后就在佛堂中,各坐一个蒲团,抵膝密语。
即令如此,胡元规说话还是有保留的。他只告诉胡宗宪,从杭州到松江,有凡个志同道合的徽州巨商,决心在通倭的海盗中策反驱倭,已经秘密部署了一年之久。此事甚难,牵涉的范围又广,所以不求速效,只求踏实。点点滴滴下功夫,则水到自然渠成。
胡宗宪既惊且喜,紧眨着双眼并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,料定柘林贼巢中,已有胡元规的人埋伏在那里,眼前就可利用。“好极,好极!你们有为有守、有财有势,大事必成,我愿随骥尾。”
“三爹太客气了!”胡元规略有不安“我们要防打蛇不成,反被蛇咬,所以步步慎重。有时候想借官府的势力借不着;如今有三爹来主持,事体比较省力。不过,也不可以操之过急。”
“当然!露了奇绽,倭寇海盗专找了你们来,确是‘家奇人亡有馀’。你们放心,我一定格外小心。”
“谢谢三爹!”胡元规说“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。”
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我们细细商量。”
名为商量,其实是提出要求。首先,胡宗宪当然也要说一说心里的话;他的靠山是赵文华,而赵文华与张经不睦。如今永保土兵已到,张经将大举攻剿,倘或建立大功,则相形之下,赵文华在朝中说话的分量就轻了。甚至调回京里,亦在意中。到那时,胡宗宪的处境艰难,不问可知。
“所以,我必得帮赵侍郎先搞点名堂出来,至少要把田州兵所丢的面子找回来。”胡宗宪提出要求:“元规,你们在柘林定埋伏了人在那里,能不能帮我一个忙?”
胡元规想了一下问道:“怎么帮法?”
“把倭寇海盗的虚实告诉我。”
“这不一定能办得到。我先请问三爹,你知道了那面的虚实,又怎么样呢?”
这句话将胡宗宪问住了,想了半天,叹口气说:“张总督把我当作眼中钉,决不会派一支兵给我,晓得对方的虚实也无用。如果告诉了他,是助他成功,我又于心不甘。元规,你看,有何善策?”
“三爹都没有好主意,我哪里有。”胡元规沉吟了一会说“这样,三爹请先回公馆。我回头派一个人去;三爹有什么话问了他再说。”
“好!”“不过,只能三爹一个人跟他谈。”
“那何消说得。”胡宗宪问道:“你将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?”
“现在还不知道哪一个来,大概姓李的一个后生。”
原来埋伏在贼巢中的人,还不止一个。胡宗宪越发心喜,告辞而归,特地关照心腹跟班长寿守在门房里,一等姓李的小后生到,直接带到书房来见。
姓李的小后生,至多20岁年纪;神情很怪,一脸稚气,独独生了一双老熟异常的眼睛。胡宗宪不敢怠慢,亲手挪开一张凳子,请他坐了说话。
“小弟弟,你叫什么名字?”
“我有两个名字。一个大家晓得的,叫李同,另外一个只有你老跟胡朝奉知道,叫阿狗。”胡宗宪一听就明白是关照不能叫他李同。他人提李同,也要装作不知其人。用这样含蓄的方式说话,足见不凡,便越发刮目相看了。
“哪个是你的真名?”
“阿狗。”
“喔!”胡宗宪笑道“我们徽州人用这个小名倒不多。”
“我原是杭州人。”阿狗用杭州口音回答“从没有去徽州。”
胡宗宪大为惊奇“你从没去过徽州?”他有些不信“说得这么一口纯粹的徽州土话?”
“跟朝奉学的嘛!”阿狗露齿而笑,稚气可掬。
“你很聪明!”胡宗宪问道:“你知不知道胡朝奉让你来见我,是为了什么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阿狗答说:“胡朝奉只告诉我,你老要问的话,只有我能回答。”
胡宗宪细想了一下,恍然大悟,这阿狗就是埋伏在贼巢中的“自己人”他所负的任务极重,而年纪却又这么轻,似乎不大相称,因而有些踌躇,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充分信任这个孩子?
他觉得必须作一个考验,而仓卒之间,又想不出较好的考验方法,唯一可行的是,看一看阿狗的耐性与定力,于是他说:“你坐一会,我去拿样东西你看。”
胡宗宪起身出了书斋,顺手将房门带上。履声渐轻,绕过回廊,却又贴着脚,毫无声息地转到前面,从窗户缝隙中静静窥探。
在胡宗宪的想象,年轻人的好奇,沉不住气,阿狗一定会东张西望,打量书斋内的古玩字画,东摸摸西看看,甚至也可能偷开抽屉。这样子等得久了,就会焦躁不耐,满屋转磨似地走个不停。
谁知一样都不是。阿狗竟如老僧入定般,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。这太出胡宗宪的意料,惊奇之余,深为满意,觉得完全可以放心了。
。反倒用责备的口吻,大声说道:“你身为前敌主将,既然见得到此,何可坐视不救?”
俞大猷一愣,旋即恢复了平静的脸色“我尽我的力量。就不知道可不可能救得回来?”说罢,起身吩咐:“备马!”
“俞将军,”赵文华挽住他的衣袖问“你去督战?”
“不敢说。但盼田州土兵还没有跟倭奴接仗,能到青村与邹游击会合。等我到了那里,看情形再说。”
“如果已经接仗了呢?”
“那就凶多吉少了!如今只能盼望一个情况,田州兵的位置占得好,是在北面;那样子才有希望驱倭入海,然而,难,难!”
“怎么呢?你看田州兵不中用?”
“占地利,失天时。”俞大猷望一望空中“‘四月南风大麦黄’,田州兵如果占住北面,就是逆风作战,显然不利。”
等俞大猷赶到青村,局势已经为他不幸而言中了!通倭的那名向导,故意将田州土兵引入柘林之西,漕泾的一个渔村;倭寇海盗,早有埋伏,拦腰截击,将田州土兵冲作两段,前一段被包围;后一段为敌人的强弓硬弩所阻挡,进既不可,退又怕敌人临背追击,只能凭藉一片竹林,勉强守在原地,成了相持不下之势,而实有进退维谷之窘。
幸好俞大猷所派的传令校尉,跟后一段联络上了;于是折而往东北,退向青村一带。倭寇海盗的实力并不充足,持着“赊一千不如现八百”的想法,放过后一段,集中兵力去“吃”前一段。在青村,对于漕泾方面的战况,还不明了,但凶多吉少,已是不卜可知的了。
“邹兄,”俞大猷向刚从闽行来赴援的邹继芳征询意见“你看被围的田州兵,该不该救?救不救得回来?”
“救当然该救。不过救不回来,再拿救兵失陷在里头,就会牵动大局。将军,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。”
俞大猷暗暗点头。邹继芳的所见略同,便可以作断然处置了。“大局一定要顾到。壮士断腕,不失为明智之举。”他说“我们要防敌人乘机反扑,集中人马守几个口子。”
守几个口子,就是守大路上的几座桥。当时议定,两方面的兵力合在一起运用,邹继芳主外,带兵增强防务;俞大猷主内,安置吃了败仗的田州兵,不让他们的锐气折伤得太利害。
到了傍晚时分突围而出,成了散兵游勇的田州土兵,陆续由邹继芳派人护送到青村。俞大猷亲自带人照料,给食裹伤,殷殷慰问。同时问起战况,才知道900多人阵亡了一半,其中有14个头目,包括钟富在内,被俘与逃出来的,大约各为一半之一半。损失真是相当惨重了!
这是赵文华轻举妄动的结果。俞大猷责任所在,不能不星夜驰报张经。正在灯下与幕友商酌军报时,瓦婆婆由胡宗宪陪着,赶到青村看田州土兵和俞大猷。
两位来客的脸色不同,胡宗宪泰然,而瓦婆婆凝重,眼圈红红地,已经哭过一场。俞大猷本想责备她几句,这么大年纪,何以一点定力都没有,轻易听人指使?见此光景,改了口气,反倒要安慰她了。
“胜败兵家常事。”俞大猷亲自搀扶着她说“瓦婆婆不必难过!”
“我怎能不难过?我的娃子们死得冤枉!”瓦婆婆厉声说道:“倭寇海盗虽多,田州娃子拚得过他们,只可惜,紧要关头借不上力。”
俞大猷见她疾言厉色的神情,未待通事翻译,心知不妙;听完翻译,更知瓦婆婆是受了赵文华的先人之言,特来指责他不发援兵,这可得辩个清楚。
这是很可气的一件事,但俞大猷还是忍住了。一则,他到底读过些书,懂得养气的道理;再则,保靖兵已在途中,一旦到达,十道进兵,痛剿清洗,可以一劳永逸,当此紧要关头,真所谓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为了期望田州土兵还能大大地出一番力,此时当然需要安抚。
因此,他平静地答道:“瓦婆婆错怪我了!事先我并不知道贵部有进兵之议,今天一早由赵侍郎亲自来通知,立刻发兵支援,毫无耽搁。瓦婆婆请想,如果不是我派兵接应,贵部出击的队伍,何以都能齐集在此?”
听这一说,瓦婆婆无话可答。其实,她作此指责,亦是一种姿态,主要的是让她的部下知道,她是在替他们诉苦喊冤。坏是坏在向导身上,然而这又是个哑巴迷!向导秉命而行,钟富带队,究竟跟向导说了些什么?如今死无对证,再也分辨不清楚了。
“瓦婆婆,”胡宗宪当然知道自己误事,不过不能也不必承认,只安慰她说:“田州兵忠勇可佩!无论胜败,人死不能复生,只有打点精神,为阵亡弟兄报仇、雪耻。”
“打仗原是要死人的!”瓦婆婆答说“我难过的是,将帅心不起,我的娃子死得有点不明不白。这也不去说它了,如今我只有一句话:从今天气,田州兵不单独出队了!要打大家一起打。”
“原就是这话!”俞大猷赶紧接口“倘或瓦婆婆接到赵大人的命令,先跟我商量一下,就不会有这样的挫折了。”
胡宗宪在一旁默默听着,颇为后悔,应该劝赵文华慎重。如今听瓦婆婆的话风,有些变通了,不再是前两天那种报答恩遇,虽死不辞的态度。倘或追究此番失利的责任,只怕赵文华还真难辞其咎。
“怕什么,先下手为强!”赵文华的脸色很阴沉“让田州土兵出击并没有错,他们打得很好;坏在向导不得力。”他急忙又说:“这不能怪你,要怪他们;倘或不是按兵不动,自老其师,凡事可以商量,就可以找俞志辅去要向导,不就打了胜仗回来了吗?”
“是。”胡宗宪很沉着地问:“大人打算如何下手?”
“我要动张廷彝!”
“只怕动不了!”胡宗宪说“我看,保靖兵一到,也会打个大胜仗;那时候就该他神气了。”
“他要神气?神气些什么?”赵文华想了好一会,面露狞笑“你看我的手段!我要教他败了不得了;胜了更不得了!汝贞,你信不信?”
“大人的话,何有不信之理。不过,才具短,看不透大人的深处。”
赵文华已经想到一个说法,但正当要开口细谈时,忽然转了一个念头,自觉胡宗宪处处比自己强,即令他非常知趣驯顺,就眼前来说,决无遭受反噬之虞,却仍应拿“逢人只说三分话,未可全抛一片心”这两句俗语为戒。而且看他有些不明白,何以张经“打了败仗不得了,打了胜仗更不得了?”
那就让他纳闷去;等降罪张经的上谕下来,也教他看看自己的手段!
毕竟还是自己比胡宗宪高明!赵文华在心中得意自语,表面上却很矜持“也不知能扳得倒他不?”他说“尽力而为吧!”
等胡宗宪一走,赵文华随即将自己关在书斋内,静悄悄地草拟奏折,主旨是攻击张经拥兵自重,能够力战而故意不战;为的是可以不断向朝廷需索,向地方勒派,在粮饷上侵吞肥己,照张经的打算,寇如饥鹰,饱则远扬;到倭寇海盗撤退以后,张经才会追剿馀寇,假报大捷,虚冒战功。
这一来,张经如果打了败仗,倒可反证赵文华的奏劾,并无根据;一打胜仗,恰好证明了他的看法不错,坐实了张经有意冒功。
田州土兵的受挫,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恶劣影响。倭寇海盗对于在西南瑶壮苗子,了解不多,只当他们如同出押之虎,凶猛非凡,以趋避为吉。哪知一仗打下来不过尔尔!然则畏他何来?
就因为这一念的转移,便又大举骚扰掳掠;由海入江的南通州、狼山、常熟、江阴,无不大遭荼毒。警报一日数次,报到嘉兴,张经急得跳脚,除了大骂赵文华打草惊蛇,误国害民以外,别无作为。因为包围聚歼的方略是早经决定了的,一切部署都本着此宗旨进行,为山九仞不能功亏一篑,否则不就跟赵文华的浮躁轻率,有何不同?
而赵文华却放不过他。为了不愿看张经的“老前辈”的脸色,他只用文书督促;一天至少一通,甚至两通,三通,文书中的措词,大同小异,第一段是引叙战报,某处被侵,死伤多少,财产损挫几何?第二段是谈总督的责任是保境安民;捍御外侮;而张经受恩深重,决不忍坐视不问。第三段是恭维以后的指责,说某处某处乞援“督辕”不发一兵一卒;现在大军云集,不难灭此跳梁小丑。何以按兵不动,实难理解。
最后一段便是要求从速出兵,传述皇命以外,往往还要“为民请命。”
连损带嚣,文字犀利刻薄,张经看过一两通以后,气得再也不看了。当然也谈不到有何复文——这原在赵文华意料之中,明知不会有结果而乐此不起,无非为张经将来下狱受审时,留下许多不利的证据而已。
这样到了四月廿几,水顺、保靖的土兵终于开到了。永顺、保靖的土司都姓彭,一个叫彭翼南、一个叫彭盖臣,官号称做“宣慰使”都很能干,亦都善于带兵,部下久经训练,不容易打得散。不像田州土兵为乌合之众,能胜不能败,一败就溃。
这也就是张经必得等这两支到了,才肯动手的缘故。事先,张经将卢镗由浙东调到嘉兴,专门负责指挥永顺、保靖土兵;同时指定驻扎在无锡、常熟一带,因为大军云集浙西,地方负担过重;无锡、常熟等地亦是膏腴之地区,可以养得起这两支土兵。
在柘林至川沙的倭寇、海盗,本来有两万多人;一部分流窜各地,也还有15000人左右。他们也早就了解张经的方略,所以等永保兵一到,知道生死存亡所击的一场大战,迫在眉睫了。
就在这时候,汪直已由日本的五岛列岛,专程抵达柘林。此来本是观察动静,恰好赶上情势如箭在弦上之时,便顺理成章地作了发号施令的大头目。浙西的地形,他相当熟悉,在研判来自各地的谍报以后,发现官军的部署,着重在南面沿海自金山卫至海盐一线,以及北面的沿长江南岸各地,中路青浦、松江到嘉善、嘉兴各地,并没有多少兵力,而嘉兴是张经驻节之地,倘或能够发动奇袭,活捉张经,固然可以瓦解官军的整个攻势;即使不能如愿,至少张经会求调西龙两路的军队回嘉兴。那一来南面沿海的防务就会出现漏洞,岂非可乘之机?
这是先下手为强的做法,倭寇海盗的头目,全都赞成。于是汪直挑选了两千人,编成一支奇袭的队伍,在已过下弦,月黑风高的4月27,由青浦、松江之间的一条小路,往西直扑嘉兴。
在汪直到达柘林的第三天,胡宗宪即已知道这个“同乡”的行藏。以后,汪直定计以及从那一天气照计行事,亦无不了然。
是一个偶然的机缘,碰上一步鸿运,可也是胡宗宪内疚于心,力求补过的报酬——误用了那个汉奸作向导,以致于田州土兵吃了大亏,虽没有人公然指责,甚至还不知道他在无形中犯了极重的过失,可是胡宗宪却不能原谅自己。觉得唯有狠狠收拾倭寇海盗一番,才能使自己宁贴、他人尊重。
可是,他所能在军事上发生的作用不大。张经和李庭彝都已经对他怀疑,采取戒备的态度。想领一军好好打胜仗,已成妄想;张经甚至于连召集将佐,听取报告的集会,都不要他参加。这样,要想建功雪耻,就非另辟途径不可。
也是得来的灵感:敌人能派间谍到这面来,这面又何尝不可仿其道而行之,也派间谍到那面去?
难的是那里去找这样一个间谍?想来想去,只有同乡可以信任;因而微服私访,访的是一个典当的“档手”
“档手”就是掌柜的大朝奉。此人名叫胡元规,是苏松诸府中徽帮商人的领袖之一;也姓胡,与胡宗宪是五服之外的疏族,照家谱排辈分来,要矮两辈;胡宗宪行三,因此胡元规管这位比他小10岁的叔祖叫“三爹”
“三爹今天怎么得闲?”胡元规迎着他说“湘西的苗子开到了,快打仗了吧?”
“你知道湘西苗子来打哪个?”
听得这一问,胡元规心中一动,不过声色之间,毫无异样。“不是打倭寇吗?”他问。
“非也!打我们徽州人。”
“三爹,”胡元规急忙提高了声音说“今天我有真正的四鳃鲈,家乡又新来一个厨子。吃酒、吃酒!”
延至密室,胡元规方始明白相告,柘林与倭勾结的海盗,因为汪直的关系,颇多徽州人,经常潜入松江城内,到各当起来访同乡。他怕胡宗宪谈下去会涉及军事机密,泄露了非同小可,因而乱以他语。是一番谨慎的好意。
这就对路了。胡宗宪在想,开口便知不是汪直一党,尤其难得的是,谨密机警,正是可共腹心的人。因而便说了连在赵文华面前都不肯说的话,当然,也发泄了在他人面前不便发泄的牢骚。
“徽州人该死!到处挨骂。”胡宗宪愤然跺脚“开当铺,道是剥削小民,没有人说,救了穷人的急。如今为了一个汪直,我们徽州人在别人眼里,都是汉奸,不过——”他的声音突然软弱了,倒仿佛为人当胸捣了一拳似地“也难怪!”
“三爹!”胡元规扶着他坐在炕床上首,自己拉张骨牌凳坐在他身边,低声说道:“我也听了些闲言闲语,说张总督是福建人;福建沿海通倭的乡绅很多,张总督怕得罪他们,不敢上紧剿倭,如今莫非因为汪直是徽州人,大家也疑心三爹?”
“我不知道别人对我怎么个想法,只觉徽州人抬不起头来。”
“是的。”胡元规黯然摇头“没有法子!”
“怎么叫没有法子?什么是没有法子?”
“怎么能让徽州人抬起头来?我想想,没法子!”
“笑话!”胡宗宪的精神又振作了“如果徽州人不通倭,为什么抬不起头来?如果徽州人能够平倭,那就不但抬得起头,还可以扬眉吐气。”
胡元规倏然抬眼,怔怔地看着胡宗宪;四目相视,无形中出现了一种剑拔弩张的情况,而终于彼此都看到对方心里了。
“你有能让徽州人扬眉吐气的法子?”
“这还不敢说。不过,三爹,”胡元规说“也有同乡跟三爹的想法差不多;只不过没有三爹这样手握‘尚方宝剑’,想也是白想。”
“如今谅不是白想了!你们的想法,只要行得通,一切在我。”胡宗宪说“就怕不切实际!即使行通了,于大局无补,亦是枉然。”
其实,胡元规的一切,不免做作。有血性、重廉耻的徽州人,亦是不少,胡元规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有他们的为国除害、为乡雪耻的计划;但却不愿与官府合作,因为朝中奸臣当道,有作为的督抚,往往不为所容,结果徒受牵累——徽州人经营典当、经营盐业,都是有身价的巨商。一受牵累,事业瓦解,不仅仅“一家哭”;依附在这事业内外的人家,少则数十,多则数百,亦失所恃,这关系太重,不能不格外慎重。
然而胡宗宪的情况不同。第一、是徽州同乡,胳膊不会朝外弯;其次,他有才气、有气力,能办大事;第三、跟赵文华处得很好,一旦放手大干,朝中不会有人掣他的肘。可是,汪直也是同乡,胡宗宪对他的态度又如何呢?
如今是很明白的了,也很可以放心的了。不过,他亦不愿意将一场大功勋轻易送给胡宗宪,至少限度要取得胡宗宪的承诺,决不泄密,亦决不会独断独行,免得措施不善,累及同乡。
打定了主意,胡元规脸上自然而自然地出现神秘而郑重的表情“三爹,”他用低沉的声音说“我想告诉你一点事,不过要请三爹先在菩萨面前立誓,决不会害我们。”
胡宗宪听得这话,兴奋而困惑“你这叫什么话?”他说“我为什么要害你们?”
“不是说三爹存心要害我们,是怕无意中泄露一句话,或者举动稍疏忽一点,替我们招来冤家,那就家奇人亡有余了。”
有这样严重的后果,胡宗宪觉得他的要求并不过分。胡元规信佛,特辟一座院落,供设佛堂;胡宗宪拈香下跪,立下誓言,决不相负。然后就在佛堂中,各坐一个蒲团,抵膝密语。
即令如此,胡元规说话还是有保留的。他只告诉胡宗宪,从杭州到松江,有凡个志同道合的徽州巨商,决心在通倭的海盗中策反驱倭,已经秘密部署了一年之久。此事甚难,牵涉的范围又广,所以不求速效,只求踏实。点点滴滴下功夫,则水到自然渠成。
胡宗宪既惊且喜,紧眨着双眼并将他的话细想了一遍,料定柘林贼巢中,已有胡元规的人埋伏在那里,眼前就可利用。“好极,好极!你们有为有守、有财有势,大事必成,我愿随骥尾。”
“三爹太客气了!”胡元规略有不安“我们要防打蛇不成,反被蛇咬,所以步步慎重。有时候想借官府的势力借不着;如今有三爹来主持,事体比较省力。不过,也不可以操之过急。”
“当然!露了奇绽,倭寇海盗专找了你们来,确是‘家奇人亡有馀’。你们放心,我一定格外小心。”
“谢谢三爹!”胡元规说“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。”
“我知道,我知道。我们细细商量。”
名为商量,其实是提出要求。首先,胡宗宪当然也要说一说心里的话;他的靠山是赵文华,而赵文华与张经不睦。如今永保土兵已到,张经将大举攻剿,倘或建立大功,则相形之下,赵文华在朝中说话的分量就轻了。甚至调回京里,亦在意中。到那时,胡宗宪的处境艰难,不问可知。
“所以,我必得帮赵侍郎先搞点名堂出来,至少要把田州兵所丢的面子找回来。”胡宗宪提出要求:“元规,你们在柘林定埋伏了人在那里,能不能帮我一个忙?”
胡元规想了一下问道:“怎么帮法?”
“把倭寇海盗的虚实告诉我。”
“这不一定能办得到。我先请问三爹,你知道了那面的虚实,又怎么样呢?”
这句话将胡宗宪问住了,想了半天,叹口气说:“张总督把我当作眼中钉,决不会派一支兵给我,晓得对方的虚实也无用。如果告诉了他,是助他成功,我又于心不甘。元规,你看,有何善策?”
“三爹都没有好主意,我哪里有。”胡元规沉吟了一会说“这样,三爹请先回公馆。我回头派一个人去;三爹有什么话问了他再说。”
“好!”“不过,只能三爹一个人跟他谈。”
“那何消说得。”胡宗宪问道:“你将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?”
“现在还不知道哪一个来,大概姓李的一个后生。”
原来埋伏在贼巢中的人,还不止一个。胡宗宪越发心喜,告辞而归,特地关照心腹跟班长寿守在门房里,一等姓李的小后生到,直接带到书房来见。
姓李的小后生,至多20岁年纪;神情很怪,一脸稚气,独独生了一双老熟异常的眼睛。胡宗宪不敢怠慢,亲手挪开一张凳子,请他坐了说话。
“小弟弟,你叫什么名字?”
“我有两个名字。一个大家晓得的,叫李同,另外一个只有你老跟胡朝奉知道,叫阿狗。”胡宗宪一听就明白是关照不能叫他李同。他人提李同,也要装作不知其人。用这样含蓄的方式说话,足见不凡,便越发刮目相看了。
“哪个是你的真名?”
“阿狗。”
“喔!”胡宗宪笑道“我们徽州人用这个小名倒不多。”
“我原是杭州人。”阿狗用杭州口音回答“从没有去徽州。”
胡宗宪大为惊奇“你从没去过徽州?”他有些不信“说得这么一口纯粹的徽州土话?”
“跟朝奉学的嘛!”阿狗露齿而笑,稚气可掬。
“你很聪明!”胡宗宪问道:“你知不知道胡朝奉让你来见我,是为了什么?”
“我不知道。”阿狗答说:“胡朝奉只告诉我,你老要问的话,只有我能回答。”
胡宗宪细想了一下,恍然大悟,这阿狗就是埋伏在贼巢中的“自己人”他所负的任务极重,而年纪却又这么轻,似乎不大相称,因而有些踌躇,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充分信任这个孩子?
他觉得必须作一个考验,而仓卒之间,又想不出较好的考验方法,唯一可行的是,看一看阿狗的耐性与定力,于是他说:“你坐一会,我去拿样东西你看。”
胡宗宪起身出了书斋,顺手将房门带上。履声渐轻,绕过回廊,却又贴着脚,毫无声息地转到前面,从窗户缝隙中静静窥探。
在胡宗宪的想象,年轻人的好奇,沉不住气,阿狗一定会东张西望,打量书斋内的古玩字画,东摸摸西看看,甚至也可能偷开抽屉。这样子等得久了,就会焦躁不耐,满屋转磨似地走个不停。
谁知一样都不是。阿狗竟如老僧入定般,坐在凳子上闭目养神。这太出胡宗宪的意料,惊奇之余,深为满意,觉得完全可以放心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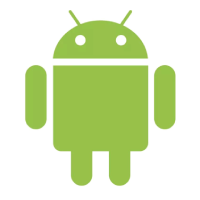

 ,然后点击“添加到主屏幕”
,然后点击“添加到主屏幕”